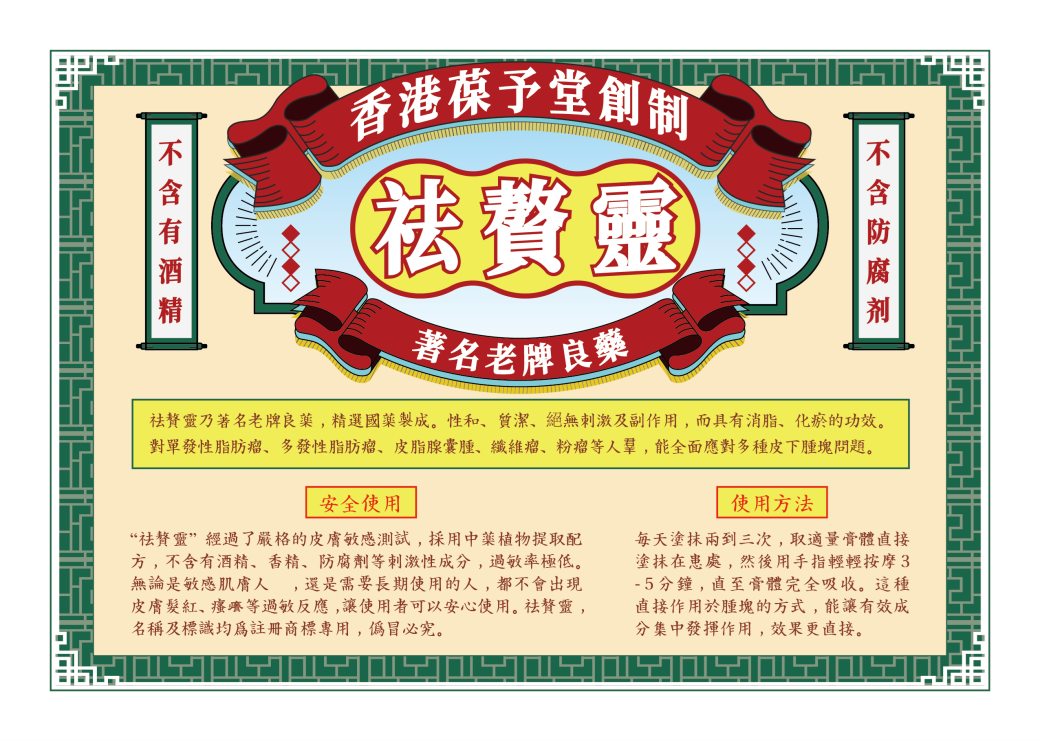张勇
现在每个人如同都在繁忙。当他们没有在作业,或是没有在做有利于作业的工作时,就会着急,心生负罪感。就连孩子们也都是大忙人,他们的时刻组织准确到了以半个小时为单位。每天当他们回到家时,跟大人相同累。
凌乱喧嚷是喧嚣的外在体现,其本质则是浮躁,是人们心里的烦躁、失衡、不沉稳。浮躁,是损失定力,趁波逐浪;是心急如火,投机取巧;是踏实夸大,一片泡沫;是不要进程,只需成果。
韩国的一项长时刻盯梢试验显现:长时刻身处节奏过快、喧嚣的环境,少年易患上注意力不会集、多动症等疾病,成年人逻辑推理才干会弱化,主管短期愉悦的细胞会更生动。美国的脑科学研讨也证明:长时刻守静有利于神经细胞轴突的延伸,有利于信息在脑细胞中的存储、分辩、比较与联络,有利于提高记忆力、剖析力、判断力与决议计划力。这些恰恰应验了“水静极而形象明,心静极而才智生”“非安静无以致远,非恬淡无以明志”许多中华古训。
《道德经》里讲,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”“轻则失根,躁则失君”。人活一辈子,要想给社会、给后人留下点东西,要想完成自我价值,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,回绝外来的引诱,祛除心里的烦躁,静下心定下神,扎扎实实、专心致志地干事,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威胁。
苏东坡趾高气扬时,虽也是才华横溢,但在离心离德的朝廷,写就的文章也不过是应景之作。当其艳丽的日子堕入谷底,瞬间只剩下一片暗淡之色。无车马之喧,也无恭维之言。安静,安静得没有半声问好,只闻自己的心跳;沉积,沉积得没有一丝亮光,只要泥土的色彩。所以思想在绵长的安静中,发酵成地力旺盛的土壤,渐渐地有了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”的豁达豪宕,也就有了《赤壁赋》与《赤壁怀古》的永存篇章。
明代洪应明的《菜根谭》说:“从静中观物动,向闲处看人忙,才得超尘脱俗的兴趣;遇忙处会偷闲,处闹中能取静,就是安居乐业的时刻。”静气是坚持清醒,镇定考虑,远见卓识,冷静应对,研讨总结经验,反思超越自我,鉴六合之精微,察万物之规则。
当年沈从文下放于湖北的干校,心里本已衣不蔽体,但看到荷花,仍然毫不犹豫地给表侄黄永玉写信说:“这儿的荷花真好,你若来……”而诗人方令孺相同有着一颗安静之心。听说,在青岛大学教学时,方令孺与闻一多志同道合,闻一多曾为方令孺写下了《凭仗》《奇观》。但是对这段阅历,方令孺一向避而不谈,只在晚年对学生说:“闻一多的诗‘半启的金扉中,一个戴着圆光的你是写我的。”上面这两个人都是抵达了安静之境的。没有安静,沈从文不会有对磨难的耐性接受;没有安静,方令孺就没有对从前一段真情的三缄其口。
林清玄从前忙于浮世里的各种热烈,开不完的会、停不了的觥筹交错。日子热烈得似起风的海,浪花飞溅。但是就在他工作走到最高峰、生命最喧哗时,他决然地转了身,到深山里的一座禅院清修。两年多的时刻里,从未下山,隔离了万丈红尘。晨钟暮鼓,在一册册经卷里沉潜。生命是一泓秋日的静水,深不见底。现在的林清玄,不管出现在任何场合,都是一派品格清高。他说:“咱们如果有颗安静的心,即使是静静坐着,也能够感受到时刻一步一步从心头踩过。”
《论语》有 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”,一般的解说是,聪明的人喜爱水,仁慈的人喜爱山。南怀瑾以为,此句应是“知者乐,水;仁者乐,山”。知者的高兴,就像水相同,悠然慈祥,永远是生动的。仁者的高兴,像山相同,崇高、巨大、安静。不管“知者”“仁者”,都离不开静的性格。人间的每一件事,要处理妥当,本来至关紧要的,是自己的心里深处是否平缓。
“天清江月白,心静海鸥知。”心里的安静,是最为深沉的修行。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,只要安静的魂灵才干生出翅膀,安闲翱翔。